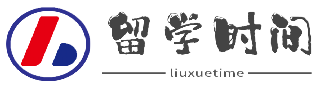荷兰汉学家艾维德:让中国的通俗文学在西方汉学的C位出道。
2024-02-10 21:33:07来源:西游留学网作者:智库News 阅读量:7163
▲2017年,艾维德教授在中山大学参加“纪念王缉思、董梅侃诞辰110周年与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并做主题演讲。
▲艾维德教授与广州中山大学歌剧研究团队成员共进晚餐。前排左起为康宝成教授、黄天吉教授和艾维德教授。
1968年大学毕业后,艾维德在汉学领域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2000年前,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2000年至2013年,加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他可谓是在欧洲汉学和北美汉学两大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艾维德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翻译成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他被认为奠定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

大唐狄公案让他爱上了中国文化。
艾维德在接受杜南记者采访时说,最早让他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的是美国女作家、诺奖得主赛珍珠的小说《群芳亭》和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小说《大唐狄公案》。高罗佩是一名荷兰职业外交官。虽然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将流芳后世的是他这位业余汉学家的成就。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他的侦探小说《唐朝的侦探案》成功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六七十年代风靡西方。“高中结束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学习一门语言,学习一种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不仅尽可能地不同于我的母语和文化,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生命力。所以我选择了中文。”
在莱顿大学学习期间,艾维德迷上了明清白话小说,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早期白话小说版本的研究作为题目。而让他在国际汉学界声名鹊起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则源于他的日本留学生涯。“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田中健二教授为我和其他一些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元戏剧阅读班,让我第一次涉足中国戏剧的研究。”
易对《西厢记》、《袁》、《汉宫秋》和《失魂的新娘》等元杂剧的英译被欧美学术界视为研究中国古代戏剧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艾维德还参与了《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剑桥文学史》等的编纂工作。此外,艾维德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女性文学课程。2004年与贝亚塔格兰特教授合编《潼关:中华帝国女性文学》,2009年合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女性作品集》。
热爱通俗文学,尤其是版本。
艾维德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通俗文学,对中国民间文学和说唱文学有独到的见解。他的研究领域也很广阔,有些说唱文学甚至是国人很少听说的,比如宝卷。他出版了《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宝典》。“我对宝卷的兴趣,不在于它是明清新兴宗教或教派的圣书,而在于它对很多民间故事,包括宗教故事的说唱演绎,比如孝子的传说,妙善公主的传说。”他幽默地说,《宝卷》对译者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就在于他们有限的篇幅:我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雷锋宝卷》的翻译并找到出版商,而《易遥传》的翻译需要很多年,出版的几率很小,因为太长了!当然,我希望我翻译的宗教传说也能起到教授中国宗教的作用。”
在研究过程中,艾维德特别重视版本的意义。他认为,对传统戏剧作品版本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对人物的考证和修改,也不应局限于对作家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研究,而应受到版本演变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学者倾向于将这些差异视为‘相似’,但让我与众不同的是,我对这些‘小差异’着迷。当我们考虑戏剧改编时,这些差异变得更加迷人。但是,有一点不同: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部剧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故事主题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比较过同一个题材的不同剧。”
采访:“传统的”中国戏曲也一直在变化。
杜南:你和如谷教授合著的《中国戏曲资料(1100-1450)》主要是论述元代戏曲的。你怎么看待它的作用和价值?
Ive:传统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传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的戏剧也是如此。你不能先验地假设19世纪的表演条件和13世纪的表演条件大致相同。所以,要想知道元曲是怎么演出的,就得研究一下元代剧场的情况:我们对演员和女演员了解多少,对观众了解多少,对演出场地了解多少。收集相关资料后,你会发现元朝和明朝初年与明朝末年大不相同,而167世纪与189世纪大不相同。所以我还是觉得《中国戏剧资料》(1100-1450)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戏剧,想更多了解早期表演传统的西方学生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在准备图书资料的时候,我们收录了几部和演员有关的剧本。这些剧目恰恰反映了元杂剧出版的不同阶段。当然,学者们一直都知道,明代的元杂剧经过了很大的改编,所以我们不能用明末改编的元杂剧来研究元杂剧,把元杂剧当作对元代社会文化的忠实反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和Xi儒谷一直试图向西方读者介绍元代和明初的版本,并不止一次地翻译了同一剧本的不同版本,只是为了强调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
杜南:你是把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翻译成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在您参与或单独工作的系列作品中,《西厢记》是明代弘治十一年的初版,您还翻译出版了孟姜女的《哭长城》、《化蝶:梁祝传说及相关文献四个版本》、《木兰从军》等十个版本你是怎么想到翻译这些民间故事或剧本的?你好像特别注重版本。为什么?
维德: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它可能采用“讲故事的方法”,以便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的日常口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直接取自专业作者的理想化“提示书”。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把白话文学等同于通俗文学,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通俗文化传统来捍卫自己的文学纲领。但他们所选择的作为“通俗文学”的作品,其实属于几百年来作家们热衷阅读和创作的小说和戏剧,而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通俗文学。真正对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的热闹传统感兴趣的,只有少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但郑振铎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出版时,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早已确立,并没有给中国大部分传统的韵文、说唱文学,如宝卷、弹词、鼓词等留下多少空的空间——更不用说闽南话、粤语的韵文叙事传统了。除了这些诗歌和说唱文学的书面传统,还有无穷无尽的形式,或口头文学!
当我被邀请为剑桥中国文学史写作时,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写下说唱文学和韵文叙事的一章。然而,当我想给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讲这个题目时,我发现只有少数明清说唱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英文,因为我要提前准备相关的译文。因此,我开始为英语为母语的人翻译这份材料。我开始之后,各种各样的体裁和题材,以及对每个故事的各种处理方式,让我很感兴趣:孟姜女的故事不止一个,有几十个,甚至可能上百个!其他著名的传说也是如此,比如《白蛇传》或者《梁祝》。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版本的故事,这取决于创作的时间和地点,作者的才华,流派的要求以及每个流派的具体受众。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将这些差异视为“相似”,但让我与众不同的是,我对这些“小差异”着迷。当我们考虑戏剧改编时,这些差异变得更加迷人。戏剧需要一个快乐的结局。因此,在许多本土说唱文学作品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并没有以化蝶而告终,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复活了。因此,“书呆子”梁山伯可以成为一个有男子气概的英雄,而敢于打破枷锁的祝英台可以展示她的女性气质。
但是,有一点不同: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部剧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故事题材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比较过同一题材的不同剧)。
重视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研究和翻译。
杜南:你对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非常关注。除了与管培达教授合作的《潼关:中国帝王时代的女性文学》外,还与方合著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女性文集》。请谈谈你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看法?
伊维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大部分是少数精英男性为其他精英男性写的文学,也是精英男性的活动。所以,文学作品虽然规模大,质量高,但在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只是反映了极少数中国人的感情和愿望。如果我们也对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感受和愿望感兴趣,那么女性当然应该是第一个被考虑的群体。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文学理论中出现了许多种“主义”,我认为女性主义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持久的一种。如果我早一点搬到美国,在那里开始我的学术生涯,我可能不会冒险进入中国前现代女性文学领域。因为,在北美,从90年代开始,这个领域就吸引了很多非常有能力的女学者。而在荷兰,研究中国前现代文学的专家很少,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荷兰语写一本关于中国女作家生活的书,里面有大量她们诗歌和散文的翻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专门写秋瑾这个人物的,她的悲惨命运也给了这本书一个书名:De onthoofde feministe。来到哈佛,有人建议我把它翻译成英文出版。我联系了管培达教授,因为我想让这本书更完整,因为她是研究佛教女诗人的权威。我们合作的结果就是潼关。后来在美国,我还出版了《满族女性诗歌两百年》,从19位作者的创作中精选了丰富的作品,对每位作者现有的传记资料进行了完整的翻译。我还被选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女性作品集的编辑,撰写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女作家的学术研究概述》。但首先应归功于方的编辑工作,因为她为麦吉尔-哈佛大学明清女性写作数据库做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为我国女性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为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我喜欢研究和翻译女性诗歌。他们很少被自己耀眼的学识所模糊,但很多当代男性诗人的作品却因此受损。而且他们的一些作品讲述了男性作家很少触及的性生活的一面。
杜南:你目前正在进行什么研究项目?近期有什么新的出版计划吗?
Ive:我对动物故事的兴趣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比如我翻译了一本书,里面收录了老鼠在阴间起诉猫的故事的各种改编。另一本书是关于中国文学中的各种昆虫形象。最后一篇是关于虱子在阴间起诉跳蚤和臭虫的短剧。我和一个专门研究韩国文学的同事合作出版了《金牛王子传奇》的翻译集。这个传说不仅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在韩国也有,有中文版和韩文版。最近一直在翻译蒲松龄的《聊斋山歌》。我关注的不是《聊斋志异》改故事的作品,大概是蒲松龄晚年写的,而是他早期的俚曲。我翻译的蒲松龄的《快曲》(赤壁之战后张飞刺死逃跑的曹操的故事)将于今年在《一丛》杂志上发表。目前,我正在编写《增补幸运云歌》(讲述武宗朱厚照和大同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英文版的最终版本,计划明年出版。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所谓‘西方方法’被夸大了”
杜南:你的研究领域涉及诗歌、评书、戏剧、小说、说唱文学、女性文学等。在你看来,在主题、视角、方法论等方面有哪些不同。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何不同?如何看待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
Ive:在中国学习和教授中国文学与在国外学习中国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任何一个国家,本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或多或少都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既有好处(如教学科研经费充足),也有坏处(如政府的关注或干预)。通过学习,学生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这就很难避免高估甚至夸大本国作者的倾向。然而,在中国之外,中国文学只是许多其他文学中的一种,它需要竞争来获得其他国家读者的关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必须在比较的语境下,说明中国文学哪些方面与其他文学不同,哪些方面相似。
比如,在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被视为作者感情的真诚表达,而在西方,文学首先被视为虚构。再比如,儒家和佛教哲学启发了中国文学,基督教哲学启发了欧洲文学,但两者往往是冲突的。所有这些差距都是可以弥补的,但这需要批评家、译者和读者的巨大努力。即使跨越了这些鸿沟,对于许多外国读者来说,中国人的名字仍然存在过于相似和难以发音的问题。用中文学中国文学和教中国文学是一回事,在国外学中国文学和教中国文学是另一回事。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所谓的“西方方法”是言过其实的。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但是,不考虑具体的外国背景,把中国的作品介绍给外国观众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待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很有意思但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启发。正因如此,我认为一开始就把某个方法斥为无用是不合理的。要知道布丁是什么味道,你得先尝一尝。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每次我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我都感到很荣幸。所以,当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康宝成教授找到我,提出要把我以前用中文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收入他主编的《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文选》系列时,我感到更加荣幸。
我曾多次访问中山大学。
杜南:看来你和中山大学戏剧研究团队的关系很深。你能谈谈你和这个团队成员的接触吗,比如创始人王缉思先生等人?
艾维德:任何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无论从事什么课题,都会首先参考国内同行的著作。由于数字技术,这方面比以前容易得多,只要大学能够付费订阅提供中国出版物访问的数据库。谁也不能忽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是国内同行研究的翻版: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不同,我们在发布研究成果时面对的受众的需求也不同。但优秀的汉学著作会充分尊重其所用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果我们正在与中国的同行研究同一批材料,我们当然也希望与中国的同行见面,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和如何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在80年代初与中国同行的第一次会面,以及我应邀参加的中国第一次学术会议。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学者们能够再次面对面,自由地谈论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对广州的第一印象可以追溯到1978年和1979年,当时我在这个城市做了短暂的导游。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山大学。在此之前,我去北京为北京大学和莱顿大学的学术合作做准备。当时,我已经对《西厢记》产生了兴趣,并希望有机会见到王缉思教授。然而,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和中山大学外事办公室之间的沟通存在一些问题。在广州下火车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中山大学的人来接我,但是我没有。等了一会儿没有结果,我向警察求助。在火车站派出所呆了一个小时左右。其中一个联系了学校,终于有人来接我了。由于其他活动,王缉思教授当时没有见到我,但他给我寄来了一些他刚刚出版的书签。到目前为止,我一直珍藏着这些书。2017年,我去中山大学参加“纪念王缉思、董梅侃诞辰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时,正值毕业季,所有即将毕业的学生都穿着礼服,拍摄毕业照(身着民国服饰的女生)。这真是一个场景。(完)(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周佩文
编辑:杨不高兴了。
相关文章

艺术留学中介:日本艺术留学中介哪家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
日本艺术留学中介哪家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和砚艺术留学小编结合部分同学的经验教训整理出了以下几点参考意见,提醒大家在选择艺术留学中介机构时一定要看这几点,也希望能帮到大家。 1. 看师资 老师的...
阅读: 47831

荷兰留学护照入境澳门流程:周四起,持外国护照入境人士,入境措施有调整
周四起当局调整持外国护照入境人士入境本澳的防疫措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宣布,经考虑本地的实际需要及评估相关地区疫情风险和变化后,卫生局根据第166/2022号行政长官批示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第40...
阅读: 7485

哈尔滨无犯罪英国双认证用于留学签证
哈尔滨无犯罪英国双认证用于留学签证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省份,当地的经济基础十分雄厚。汪女士是哈尔滨的,打算去英国留学,英国当地高校要求出具哈尔滨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阅读: 15399

卢森堡到荷兰留学行李多少钱:欧洲留学要花多少钱?19个国家学费、生活费总结整理
欧洲留学到底贵不贵?今天,我们总结了了北欧、南欧、西欧、中欧和东欧的19个国家的学费和平均生活费,为大家做一下参考。中欧国家德国德国一直是中国学生非常热衷的留学国家,尤其是学习商科、工科和艺术的学生格...
阅读: 8893

白月光收藏的“80年代重生第一名人”拔得头筹,含糖量超标。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身为疯狂热爱小说的书虫,小编这次又来给大...
阅读: 9527

荷兰留学回国机票美国多少钱:疫情叠加战事影响,返华国际航班价格近期或将居高不下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3月2日讯(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卢奥)疫情之下,国际航班数量锐减,从国外返回中国的国际机票价格一路飞涨。俄罗斯乌克兰军事冲突爆发后,空域制裁再对国际航线造成巨大影响。3...
阅读: 2148

西班牙飞荷兰留学费用高吗:欧洲留学性价比高的国家
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有着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并且在留学费用方面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近年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同学的留学计划被迫中止搁浅,也让不少同学对留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虽然疫情对留学申请...
阅读: 37993

三位总统虐现小说,强推《冷婚》,泪虐心脏,纸巾都哭出来了~
嗨喽小伙伴们又见面了!这次小编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小说哟,毕竟作为一个资深的老书虫,能看的入眼的小说都必须要文笔一流,剧情出彩。不知道小伙伴们做好收藏书单的...
阅读: 1508

留学去丹麦还是荷兰工作好:欧洲各国薪资水平,生活成本以及福利待遇各方面对比
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是富人的天堂。那么哪个欧洲国家工资收入最高呢?欧洲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又是哪里,哪里开车成本最高,哪国超市东西便宜...带着诸多疑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丹麦净收入最高可能薪水对于部...
阅读: 46939

【荷兰留学】2022年荷兰留学最佳申请时间
2022年准备去荷兰留学的小伙伴们都清楚荷兰留学申请费用相对低廉,且大学排名都好,所以每年申请去荷兰留学的人数非常多,对于有意向申请荷兰留学的同学来说,需要提...
阅读: 12399
更多排行榜
热门文章
1.美术留学培训机构:世界十大最顶尖的美术学院
-
1

- 美术留学培训机构:世界十大最顶尖的美术学院
- 2024-02-06
-
1
2.西班牙去荷兰留学申请要多久:高性价比“慢”节奏——比利时留学
-
2

- 西班牙去荷兰留学申请要多久:高性价比“慢”节奏——比利时留学
- 2023-12-04
-
2
3.英国留学中介:英国留学中,哪三所大学中介最喜欢拿来做保底?实际怎么样?
-
3

- 英国留学中介:英国留学中,哪三所大学中介最喜欢拿来做保底?实际怎么样?
- 2024-01-19
-
3
4.荷兰留学大学学费最晚多久交:荷兰留学一年费用需要多少?
-
4

- 荷兰留学大学学费最晚多久交:荷兰留学一年费用需要多少?
- 2023-12-16
-
4
5.留学中介:留学中介服务乱象调查,“背景提升”竟成生意?
-
5

- 留学中介:留学中介服务乱象调查,“背景提升”竟成生意?
- 2024-01-22
-
5
6.艺术留学机构:美行思远留学|艺术专业选择及院校推荐
-
6

- 艺术留学机构:美行思远留学|艺术专业选择及院校推荐
- 2024-01-26
-
6
7.艺术留学中介:日本艺术留学中介哪家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
-
7

- 艺术留学中介:日本艺术留学中介哪家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
- 2024-01-28
-
7
8.荷兰留学计算机要求高吗:2022欧洲留学|最有“钱”景专业来袭!计算机相关硕士项目推荐
-
8

- 荷兰留学计算机要求高吗:2022欧洲留学|最有“钱”景专业来袭!计算机相关硕士项目推荐
- 2024-01-04
-
8
9.留学去丹麦还是荷兰工作好:欧洲各国薪资水平,生活成本以及福利待遇各方面对比
-
9

- 留学去丹麦还是荷兰工作好:欧洲各国薪资水平,生活成本以及福利待遇各方面对比
- 2023-12-05
-
9
10.荷兰留学社科专业推荐吗:留学费用|去荷兰留学一年需要多少?同学说要两万欧
-
10

- 荷兰留学社科专业推荐吗:留学费用|去荷兰留学一年需要多少?同学说要两万欧
- 2023-11-30
-
10
一周热榜

留学邮寄荷兰快递:怎么邮寄到荷兰
2023-11-03

国际e邮宝去邮局发吗
2023-11-04

荷兰留学文化:荷兰留学全攻略,留学新热点——荷兰
2023-11-04

留学生生存必备指南(留学生如何在国外寄快递?(国际快递)
2023-11-04

瑞典留学和荷兰留学区别:盘点 | 那些留学费用相较便宜的国家推荐
202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