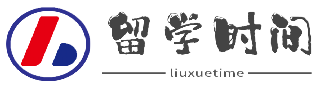教育时代的终结:从“直男癌”到“真男人”,余的体面退场。
2024-02-09 08:28:14来源:西游留学网作者:久违 阅读量:6699
我走在崩溃的边缘。

——俞敏洪
北大1987年俞敏洪在北大教书。 当时正好赶上了海外热潮。 俞敏洪身边的同学朋友,纷纷出国,让他羡慕。
俞敏洪追随潮流,复习了两个月,托福考了673分,GRE考了700分,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大学,力图走出国门。
万事俱备,只借东风,东风是什么? 是钱。
为了拿到留学经费,俞敏洪找了几家教育机构,教托福和GRE,每月收入2000,比北大工资高10倍。
俞敏洪觉得如果我自己办班,会更赚钱,于是在北大开了托福班,很快就有二三十个学生报名了。
北大也有托福培训班,俞敏洪等于挖学校的墙角。 另外,他没有证照,是“逃亡犯罪”。
北大领导找到俞敏洪,说得很难听。 双方发生冲突,俞敏洪受到行政处分,其“光荣事迹”被贴在北大有名的三角地上,贴了整整一个月,在推特上播放了一周。
在学校被处分后,俞敏洪吃了苦头。 另一间屋子没他的份儿,北大派他出国进修也轮不上他。
1990年,俞敏洪提交辞呈,用三轮车,拉起所有的房子离开北大,在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向当地的老农租了房子。
中关村二小允敏洪发现,学习英语的热潮来了,很多学生要想出国,需要通过托福和GRE。
这两个考试难度很大,特别是GRE在整个北大,也没有几个老师教。 因为——词汇需要2万人。
大学时代,俞敏洪因为肺结核,在医院躺了一年,没事做,拼命背单词。 北大毕业时,俞敏洪掌握的词汇量已经接近两万。
说干就干,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一套房子,为了招生租了一套房子,但那房子破极了,20平方米左右,一下雨就漏。
有些学生来报名了,一看到招生地点,就扭头走了。
俞敏洪到处张贴招生广告,无孔不入,特意把招生广告贴在性病广告旁边,要求流量加码,但报名者寥寥无几。
没办法,俞敏洪开始了免费试听。 他把试听场地设在中关村的两个小操场上,没有音响设备,只能扯着脖子喊,一节试听课大概有十几个人报名吧。
因为学生不多,俞敏洪时间很多,学生和他说话,他就在天南地北聊天,有时开心地聊天,让学生吃夜宵。
在这个过程中,俞敏洪发现学生们对幽默和感动的聊天方式非常有用,于是故意朝这个方向靠了过去。
做了一段时间后,俞敏洪已经出名了。 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学生都知道,有个叫俞敏洪的家伙,在做托福训练,课程不好,能胡说八道。
年轻时的俞敏洪
报名上课的人越来越多,中关村的两个小教室不够了,俞敏洪联系北大电教中心,租了一间能容纳80人的教室。
小班到了大班,同学们本以为会有意见,结果每个人不仅没有抱怨,积极性更高了,俞敏洪见状,全力解题,上大学课,说段子,卖课也卖笑。
慕名而来笑场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班改成了两个,两个班变成了四个。 面对这甜蜜的重负,俞敏洪分身乏术,不得不聘请老师。
不仅班级多了,课也大了,有一次,北大化学楼租了一间300人的教室,开课时有500人插队。 也有坐在楼梯上,头脑发热,屁股冰凉的学生。
看到这个情景,俞敏洪笑了,重招的时候,身体好了,提前打个招呼,来我这里上课。 在这种环境下,没有桌子,只有一把椅子,有时也没有椅子,可能只是坐在楼梯上。
虽然雇佣了老师,但是有时间的话,俞敏洪会尽量自己参选。 因为不用给自己发工资,也可以省钱扩大再生产。
俞敏洪怕别人老师反水,自己什么课都准备,只要保证自己是学生眼里“菜”最好吃的厨师、厨师、老板,就稳扎稳打。
虽然不能只教一门课俞敏洪,但是因为是GRE数学的逻辑,所以拜托了专家。
半年后,大佬要求增加钱,说得很有道理。 俞老师,看别的课也能教,但是只有我的课不能教,其他老师也不能教。 能帮我把钱放进去吗? 俞敏洪先生,你想加多少钱? 对方回答说,这个班收入的四分之一是我的就可以了。
俞敏洪一算,把钱放进他,其他老师也一定要放进钱。 这笔钱不能放进去。
“加钱哥”加钱不结果,直接不上课,俞敏洪只好退学费给学生,痛不欲生。 如果不让“厨师”发动叛乱,就必须安排更多的人来取得平衡。
这件事发生后,俞敏洪每节课安排了2、3名老师,GRE数学逻辑课安排了4、5人。
除了平衡的重要性之外,俞敏洪还领悟到一个重点:掌握了优秀的老师,就掌握了一切。
明白这一点后,俞敏洪让老师把工资翻了一番,同时用自己幽默动人的风格训练他们。 专业课做得不好,还可以通过努力来修复。 不能说段子,用幽默玩的话,就得打扫房子。 因此,很多来自北大的老师被炒鱿鱼了。
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办培训学校,必须有办学许可证。
当时的规定是,如果大学教授联名申请,就可以得到批准。
俞敏洪瞄准的是一家名为“东方大学”的教育机构。 该教育机构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创办,主要负责自学考试指导,没有外语培训。
俞敏洪找到这几位老教授,提出要合作办学,进行外语培训。
老教授们说,我们没有外语培训经验,许可证可以带走。 拿出利润分配方案就可以了。
俞敏洪说,东方大学的外语培训由我来完成。 总收入的25%分给你们,可以吗? 听了俞敏洪的建议,老教授们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多亏了老教授的办学许可证,俞敏洪马嗯嗯嗯嗯地干了几年,到了1993年,培训班收入达到了六百万元。 根据协议,要分给无所事事、坐以待毙的老教授们一百多万元,俞敏洪忍不住肉痛。
出于长远打算,俞敏洪暗下决心,一定要拿到属于自己的办学许可证。
俞敏洪赶到海淀区成人教育局申请办学许可证,被告知吃闭门羹,绝对不可能。
俞敏洪决定敲门,每一两周去教育局和他们聊天,跑了半年左右。 他们对俞敏洪说:“俞老师,你不是想拿办学许可证吗? 我们看到你帮了东方大学这么久,没什么。 如果你想拿到学校许可证的话,我们还能帮上忙。
俞敏洪大喜,像教堂婚礼的宣誓一样,害羞而坚定地说。
教育局的人接着说,拿学校证书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可以放宽一点。 你是北大的老师,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副教授。 这个可以计算。
但是,第二条原公司的证明必须拿来。
听了这话,俞敏洪像冰水一样倒水让他去求北大,那太难了。
教育局的人又给他下了指示,去找存放户籍文件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北京有很多人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下海。 为此,设立了存放档案的地方——人才交流中心。
如果人才交流中心想为俞敏洪出具允许办学的证明,教育局也会认识到的。
来到人才交流中心,俞敏洪碰了一鼻子灰,对方拒绝出具证明。 理由是他害怕说谎。
俞敏洪第二天又来了,在门口见到女孩子,女孩子笑着打招呼,俞老师,你在这里做什么? 俞敏洪目瞪口呆。 你认识我吗? 女孩笑了,我在你的托福班上课。
在女孩的帮助下,俞敏洪拿到了人才中心颁发的证书。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持有办学许可证。 当天狂风大作,吹落在路边的杨树叶飞舞,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心里暖暖的。
俞敏洪约老教授摊牌,以后我有证书,不能再给25%的分了。
老教授们消沉了,叹了口气。 那么,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打散,祝你学业更成功。
因为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名声大噪,俞敏洪前脚刚走,马上去找老教授,说这个名字就算我用,也会给你们25%的得分。
俞敏洪知道后,忙着又来拜访,告诉老教授,他们那个外语培训未必顺利,你们25%能不能拿到还是个问题,不如我每年给你们20万元,继续买这个名称三年,就再给别人
老教授们商量后,再次露出了温柔的微笑。
从此,俞敏洪不再以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义招生,改成了好记的新名号——新东方。
妙峰山新东方之名响起后,一些学生为了报名熬夜排队,很多外国学生晚上坐火车来上周末上课,星期天再坐火车回来。
俞敏洪的招生也有诀窍。 最早招收的学生既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紧随其后的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
申请人越多,就越容易教你高分。 新东方首先出现了用托福取得满分的人,一时成为了话题。 之后,又出现了5、6人在托福上得了满分,接下来是在GRE上得了满分,在GAMT上得了满分。
新东方可以教满分,成为了增加生源的金字招牌。 另一个金字招牌是打感动牌。 俞敏洪最擅长的是讲故事,把新东方早期教师的物质拮据写成动人的故事,化腐朽为神奇。
为了方便外国学生来北京新东方上课,俞敏洪决定开设住宿班。 也许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的辛苦意识。 或者可能是为了省钱。 地址选在妙峰山脚下的四十七中,将这里的两座废弃的房子改造成了教室和宿舍。
整个宿舍,一个厕所也没有。 俞敏洪在宿舍外面做了简易厕所。 就像传统的农村厕所,隔成一团,香气飘十里。 学生们为了听课而咬紧牙关忍耐。
有的学生开玩笑,真受不了熏,一遍遍默念新东方名言。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一定会变得辉煌。
后来宿舍不够,俞敏洪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瞄准了据说是李莲英避暑之地的废弃古庙。
这座古庙的老屋是国家文物保护的对象,俞敏洪特意征求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 文物局的人说,只要你们不动主要结构,把里面隔成宿舍也没关系。
俞敏洪听了,兴冲冲地插手李莲英的大屋,隔着几十间宿舍,可容纳一千二百人。
新东妙峰山的住宿班用了十几年,从1993年到2010年。 那里有个叫安河村的村子,村民们致富把戏,为不熟悉住在李莲英别墅的学生们盖了民宿。
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村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俞敏洪把住宿班搬走的时候,村里人很失望地堵在路上,不让他们走。
因为生意很好,新东方外语培训班一年到头都在运转,连新年都不休息,除夕、初一也上课。 俞敏洪和住宿班的学生一起过年,包了好几年饺子,乃至连续10年,没有和自己的家人过年。
说起家族,新东方曾经很像家族企业,俞敏洪的出发点还是省钱高效,既然是一家人,肉煮在一个锅里,就不用在意报酬和工时了。
俞敏洪的家庭成员,进入新东方后,不用以工作8个小时来计算,每个人都不辞辛苦,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2点,吃吃住,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家庭模式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新东方长期陷入混乱。
很多时候,俞敏洪说的话,母亲不听,妻子也不听。 同样,俞敏洪也不听妈妈的话和妻子的话,彼此各行其政,让员工陷入混乱。
普通员工为了上进,或者只是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讨好俞敏洪的家人。
因为俞敏洪率先这么做,其他新东方干部中,也来了不少临阵磨枪的七大妈,整个新东方内部鸡飞蛋打,像一场宫斗大戏。
俞敏洪和妈妈
当发展到只有亲近的人才能解决的混乱局面时,新东方高层召开会议,决定了“杯酒解释权”。
为了维护俞敏洪的面子,几个合伙人说,每个负责人的家族成员都要清除,但老俞,你不一样。 你毕竟是新东方的奠基者,而且最开始,你妈妈和姐夫已经在新东方工作了,他们也不会惹麻烦,所以你家里有几个成员留在这里,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别人家里的成员都离开了,一个也不留
俞敏洪明白,自己专门化了,就很难服众,于是快刀斩乱麻,用了大半时间,把自己家族的成员都赶走了。 因此,俞敏洪的母亲半年没有给他做饭。 俞敏洪觉得不是她的儿子。
温哥华和新泽西的1994年,新东方的年总收入超过了千万。 那时,俞敏洪从以前联系过的美国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穿着西装的俞敏洪,拿起录取通知书,看了看,最后找到了优雅的归宿——垃圾桶。
一年后,俞敏洪出国了,但没有去留学,而是找伴侣。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
俞敏洪第一站是加拿大温哥华。
俞敏洪出了海关,等了两个小时,远远地看到同学徐小平带着儿子来接他。
两人聊得兴高采烈,俞敏洪惊讶地发现徐小平在温哥华失业,那一年还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美元支票,俞敏洪为了炫耀,兑换了一万美元现金带走。
到了晚上,徐小平带着俞敏洪去吃饭了。 地点定在百货商店了。 车子通过商场入口附近的停车位也没有停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去了很远的停车位。
俞敏洪一听,知道在商场门口停车,需要两加元的停车费。
俞敏洪暗觉得徐小明的日子好像不好过。
两人说话的时候,徐小明激情澎湃,给俞敏洪唱了几首自己作曲的歌,他自己忍不住落泪。
俞敏洪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徐小平说,我的理想是回国做音乐,创办唱片公司。
俞敏洪接着说,你觉得开一家音乐公司要花多少钱? 徐小平先生回答。 大约需要30万元。
俞敏洪,那今天就决定了。 给你30万元。
但我断定你这家音乐公司赚不到钱。 如果你回去和我一起做新东方,也许能赚更多的钱。
热泪盈眶的理想主义者徐小平一听,马上说,能赚更多的钱当然好。
于是徐小平决定当晚和俞敏洪加盟新东方。 随后,他又带着俞敏洪去了渥太华的舞厅,开阔了视野。
看了渥太华的舞厅后第二天,俞敏洪直奔波士顿。 于是没有尝试龙虾,而是向朋友借了一辆车,横穿波士顿,向南行驶,向南行驶,经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曼哈顿,最后到了另一位老同学王强所在的新泽西。
王强当时混得很好。 我在有名的贝尔研究所工作。 俞敏洪向他介绍了新东方的发展情况。 年收入千万元,利润也百万元。
第二天,王强请俞敏洪去中国餐馆吃饭。 我刚到饭馆,就来了客人,有人站起来说。 俞老师,你怎么来了? 王强吓了一跳,在做什么? 这里有人认识你吗? 俞敏洪微微一笑,表情云淡风轻,他们当初在我托福班上课,现在来美国上学呢。
吃完饭,两人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散步,又有中国学生向俞敏洪打招呼。
小王的心变强了。
纽交所与合作伙伴有了更多人才的加盟,新东方业务板块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钱如潮水般滚滚而来。
半夜,几个合伙人喝着啤酒,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口号。 新东方将成为——海外留学的桥梁,成为回国创业的彩虹。
这个口号一出,新东方的感人故事,就增添了一份家人的情怀。 新东方是中国孩子出国深造,他们回国的时候,可以创造更高的技术成果为祖国做出贡献。
但是,在现实的另一端,有很多人在中国接受过最好的教育。 出国留学只是为了拿绿卡而移民,失去了很多人才。
为了探索新东方的未来之路,俞敏洪等人请来了王明夫的咨询团队。 王明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了解新东方的财务状况。
据了解,新东方年收入2.3亿元,利润约1亿元左右,于是建议他们上市。
中国上市公司平均市值是公司利润的50—100倍,如果新东方能上市,市值有望超过100亿美元。
咨询会后,新东方所有高层都欢呼雀跃,赶紧上市吧。 新东方真的价值100亿元,即使分1%的股份,也是1亿元。
俞敏洪说,既然大家都想上市,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吧。
当时的新东方是培训学校,不是成立公司,而是成立公司才能上市。
俞敏洪等人以“东方人”为名注册了公司,后来感到违和感。 但是新东方品牌不清晰,工商注册不通,俞敏洪就发挥了看家能力——。
经与工商局反复协商,新东方已是知名教育品牌,总公司名称最好与下面学校的名称一致,最后工商局终于同意,将东方人三个字改为新东方。
注册公司,其次是股权分配,对新东方有重大贡献的共有11人,经协商,俞敏洪拟取55%的股份,同时从俞敏洪55%的股份中提取10%留给后人,其余10人将分得剩余45%的股份
新东方转型的这几年,也许从2001年到2006年,新东方高层一直争吵不休,矛盾不断,但奇怪的是,新东方的业务仍然保持着每年3.40 %的高速增长。
面对这种局面,俞敏洪召开会议,提出让位辞去董事长职务,成为纯粹的股东。 董事长由王强任,副会长由徐小平任,胡敏任总裁。
这几年,吵架依然在继续,反而更加激烈。 2004年初,新东方即将在美国上市,到了关键阶段,每个人都觉得必须掌舵俞敏洪,于是把他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得知新东方将在美国上市后,美国著名的老虎基金来访。 这个基金在中国的总代理叫陈晓红,是俞敏洪的学生。
老虎基金在新东方投了3000万美元。 这和在美国市场为新东方背书一样。 当时,新东方的估值为3亿美元,老虎基金占新东方10%的股份。 之后,得到了数倍、十数倍的回报。
新东上市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俞敏洪等人登上敲钟台,只听声音,新东方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
发售当晚,纽交所举行招待晚宴,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俞敏洪红着脸,吹着酒,在晚宴上畅谈新东方如何走向未来更大的辉煌。
晚饭后,俞敏洪去了哈德逊河,看了纽约的夜色,看了全城的灯光,在河边的椅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
100年后的2012年7月,美国浑水公司发表了共计90多页的调查报告,谴责了伪造新东方财务数据、伪造教学区、伪造学生人数。
短短两天内,新东方股价从每股20多美元跌至9美元,市值缩水60%。
浑水公司总是喜欢做空中国公司,其公司名为来自中国的——浑水摸鱼。
这家公司的盈利模式是卖空。 他们深深明白,调查报告一公布,他们的“猎物”股价就惨跌,浑水公司借此机会大赚一笔。
在这个阶段,俞敏洪成立了午宴,邀请了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企业家朋友。
吃饭时,俞敏洪谈到了新东方面临的危机。 席间,老俞,你跟我们说实话,浑水公司对你的指责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充分相信你,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诉我们实话,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如果不是真的,我们会来买新东方股票,帮你找回股价。
俞敏洪说,新东方决不做假账,这是我的底线。
听了俞敏洪的这句话,企业家们,不用再说话了,喝酒吧。
当天晚上,约3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新东方的股票,仅两天就使新东方的股价回到了12美元。
此后,新东方股价在首次上市的10年间,2015年出现拐点,短期内上涨至80美元,2018年6月1日,新东方股价达到108.23美元,与2014年相比上涨359%。
2016年4月23日,当新东方股份缓缓上涨时,俞敏洪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周年专场上,俞敏洪春风满面地说。 “面向未来10年,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乐视一定会处于经济发展的视野中,但10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兴盛,这些公司可能会消失。 100年后出现了障碍,能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只有两个字,我认为就是教育。 所以,一百年后新东方一定还在。
俞敏洪在台上热烈讨论的时候,坐在台下的马云一直在摇头。 俞敏洪发现后,马云问,为什么一直摇头?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马云(杰克默)回到了路上,你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10年内不一定没有阿里巴巴等公司,3年内可能就没有了,但现在没有能脸红3年的互联网公司。
第二个逻辑错误是,有教育,新东方不一定有。 这是另一回事,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听到马云(杰克默)的回答,俞敏洪笑了,表情尴尬。
2021年,中国“双减政策”落地,教育行业迎来时代巨变,新东方股价原形毕露,暴跌近90%,市值蒸发2000多亿。
据一位风投人士透露,这条赛道基本上已经废弃了。
农民的儿子于2021年11月4日,俞敏洪在朋友圈转发文章称,教培时代结束,新东方捐赠新课桌椅给乡村学校,已捐赠近8万套。
还有一件事,俞敏洪说,新东方的账上现在有100多亿元人民币,这笔钱不会动用。 如果新东方破产了,这笔钱一个是退给家长和学生,一个是补偿遣返的员工,绝不留尾巴。
在此期间,敬允敏洪是个汉子,突然激增,蔓延到了网络上。
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中,俞敏洪弯着身子进了局,退了的体面,说实在的,确实不容易。
我对新东方的励志文化一直不感冒。 只是,我觉得从那些演说中产生的感情,都只是有效的商务手段。 说起来,俞敏洪是个善于抓住机会,也会敲门的人。 这样的人从改革开放至今层出不穷。 他们通常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名列前茅,成为站在波浪翻覆上的毁灭性孩子。 但是,如果退潮了,不管多远,也只能慌张退场。 仿佛是一句老话
但俞敏洪有一个平易近人的特质。 要说矫正,那就像金子,是温情脉脉的朴素善良。
成立初期的英语培训机构时,竞争对手的员工在贴宣传海报时,为了争夺好位置,曾用刀刺伤俞敏洪的工作人员。
后来,这家教育机构的女老板因为老师嫌弃低工资罢工,没能给学生上课,资金链断裂,也不能退款,眼看就要跳楼了。 关键时候,俞敏洪不顾之前,自己出钱让这位女老板给老师加钱,解除了燃眉之急。 这种敷衍塞责、报德仇的行为,不能说是“结构大”。
这种发自内心的善良,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承下来的最宝贵的基因,也是人类共有的最亲切最值得珍惜的爱情。
我在俞敏洪的那篇父母叙述的传记《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找到了这种善良和朴素的根源。
俞敏洪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END正文作者:哲空、血钻故事主编正文编辑:左页,血钻故事执行主编部分参考资料: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俞敏洪自述,中信出版社
相关文章

GRE为什么要在网上刷题?GRE APP是哪个?
对于GRE备考来说很多同学其实都很迷茫到底要怎么刷题,相信大部分同学都习惯于纸质做题,但是GRE自适应机考的特殊性又让烤鸡们不得不习惯...
阅读: 17459

而托福和GRE将于2023年9月28日在中国开考。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讯(记者 梁丹)近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研究商议并决定,于2022年9...
阅读: 14373

GRE考场测评:贝尚深圳等城市10大考点详细体验。
不同城市的各个考点体验如何?设备感受怎么样?交通、吃饭、住宿是否方便?以下是网友分享的在北京、深圳、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GRE考场的...
阅读: 8662


你知道2020GRE考试时间吗?去美国读研需要考多少分?
众所周知,GRE是美国大学研究生入门考试,重要性不言而喻。最近,中国教育考试网最新公布了2020年GRE考试时间,来看看自己该报哪一场...
阅读: 16070

GRE报名官网是哪个?报名GRE需要参加搜索服务吗?
各位同学们,大家都知道,GRE报名是GRE考试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其在重要性不言而喻。GRE报名的网站大家应该都已经清楚了,国内的考生的...
阅读: 5723


突然!ETS月取消北京GRE和托福考试(附申请建议)
一早,有同学收到北京10月GRE考试取消的短信!!!火速上线去了解了一下,发现ETS官网临时大规模取消北京10月份GRE、托福考试,目...
阅读: 8957

GRE备考经验分享:一战只用了三周就考了328分。
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用了三个星期备考GRE,一战328分(V1160+Q168,写作4),只是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同时膜拜下330...
阅读: 16205

2021托福,雅思,GRE,SAT全年考试安排,推荐收藏。
新年伊始,你是否暗下决心:今年一定要一句拿下托福/雅思、GRE/GMAT/SAT!尤其是申请2022年入学的同学,今天整理各大留学考试...
阅读: 13129
更多排行榜
热门文章
1.GRE在线考试记录|最新考试经验分享
-
1

- GRE在线考试记录|最新考试经验分享
- 2024-01-05
-
1
2.gre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
2

- gre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 2024-01-22
-
2
3.昨天托福考试位置秒售罄,那些说留学坏话的人又被打脸了。
-
3

- 昨天托福考试位置秒售罄,那些说留学坏话的人又被打脸了。
- 2023-11-16
-
3
4.2022年下半年考试时间,2022年下半年考试时间表
-
4

- 2022年下半年考试时间,2022年下半年考试时间表
- 2023-11-18
-
4
5.英国留学申请材料加GRE?这些大学已经发布了官方通知。
-
5

- 英国留学申请材料加GRE?这些大学已经发布了官方通知。
- 2023-11-20
-
5
6.那些雅思7分以上的学生词汇量是多少?
-
6

- 那些雅思7分以上的学生词汇量是多少?
- 2024-01-27
-
6
7.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GRE 164 167 4。经过两个月的投诉,我终于得到了有效的结果。
-
7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GRE 164 167 4。经过两个月的投诉,我终于得到了有效的结果。
- 2024-01-21
-
7
8.多林哥考试难度适应性考试机制全解析——不同环节试题难度差异
-
8

- 多林哥考试难度适应性考试机制全解析——不同环节试题难度差异
- 2023-11-11
-
8
9.GRE成绩怎么算,gre考试多少分合格
-
9

- GRE成绩怎么算,gre考试多少分合格
- 2023-11-15
-
9
10.考试前一定要考GRE模考吗?GRE模考培养什么能力?
-
10

- 考试前一定要考GRE模考吗?GRE模考培养什么能力?
- 2024-01-03
-
10
一周热榜

立正!自2022年11月起,GRE考试费全球上涨。
2023-11-03

讲完整个故事!GRE考试,那些你需要知道的干货
2023-11-04

想出国留学,GRE和GMAT选哪个好?
2023-11-04

ETS官方:11月1日提高GRE考试费用。
2023-11-04

GRE需要多长时间,考试包括哪些内容?
202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