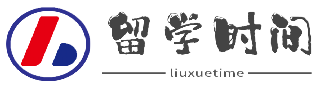李雪涛:安特生眼中的万象中国与他的《龙与洋鬼子》
2025-02-07 23:03:52来源:西游留学网作者:智库News 阅读量:18130
《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本影。 图: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百多年前的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泰生( 1874-1960 )在河南三门峡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起点。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历时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分布于今天的甘肃省至河南省之间。 在这个地区,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数以千计的仰韶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的发现改变了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论断。
1918年在河南考察时的安特生。 图: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是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仰韶文化”之外,他的名字一直与“北京猿人”等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发现有关。 民国成立不久,北洋政府于1914年聘请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勘查所所长的安特生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与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勘查所合作勘查中国铁矿和煤矿。 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略中国时,瑞典被认为是当时少数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 同年2月,英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 1887—1936 )被任命为矿务局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5年春天,两位地质学家在北京相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丁文江去世,他们也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乃至中国史前研究上的许多奇迹。 中国史前史研究的发端是中外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安特生史前考古的专业素质和丁文江的预见性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一伟大事业。
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瑞典地质调查组,右一位是安特生。 图: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特生与丁文江一起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培养了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家。 在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中原许多地层中蕴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1916年后,安特生和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点,专心收集和整理古生物化石。 这也是安特生的真正兴趣。 古生物化石采集计划促成了后来一些重大考古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河南减池仰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 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都起源于安特生。 仰韶村、马家窑等遗址出土的中原彩陶,使世界真正认识了新石器时代丰富的东亚历史。 这些震惊世界的发现是中瑞双方考古合作的结果,当时双方签订了挖掘协议,约定双方各持一半挖掘品。 安特生的研究结果需要在中国学刊《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 瑞方保管的挖掘品收藏展示在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属于中国方面的另一半挖掘品由于战乱,大部分丢失了。
1925年安特生回到离别11年的瑞典,1926年出版了《龙与洋鬼子》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对安特生的认识大部分是基于他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的身份,他的名声也是基于中国史前考古学创始人的基础。 但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安特生的名字与《龙与洋鬼子》这本通俗读物密切相关,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 试图以这本书为中心,梳理安特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安特生《龙与洋鬼子》 1926年瑞典语版。 图: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了解中国的前提
安特生不仅在中国居住了多年,而且史前考古的挖掘也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基于经验的。 一个西方人想了解中国人及其文化特质必然要先了解旧中国作为当时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国家有优越感的问题。
这种相对孤立的中国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精神,即中国是文明的国家,是高于一切野蛮王国的天下国家。 牢记这个事实很重要。 因为,只有知道这个事实,中国政治家才能理解上世纪(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无法克服的机械文化—— (我后来因“白祸”( the white peril ) ——的入侵而引起的精神混乱和深深的忧虑。
只有理解了这样一个前提,西方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时的反应。 安特生把迄今为止欧洲对亚洲民族,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使用的代表性歧视用语“黄祸”( yellow peril ),用以人之道还人之身的方法进行了改造,把西方对东亚的文化入侵称为“白祸”。 西方人的到来使革命在当时的中国不可避免。 安特生清醒地认识到辛亥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 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涵不同,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值得安特生羡慕。 他们种牡丹,养金鱼,坐在树荫下。 西方人追求外面的一切,或者用科学来改变世界。
对中国的同情理解
《龙与洋鬼子》讲述了当时中国公务员安特生在中国11年的经历。 中国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 安特生认为这是挑战时间的力量。 “人们害怕时间,而时间却害怕金字塔”,这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的谚语。 拥有肉体的我们,之所以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 时间之所以害怕金字塔,是因为尽管过去几年,金字塔依然矗立。 在金字塔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 但是,安特生有另一种看法:
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 palaces of Crete )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 pyramid )的建设者、楔形文字的先人——已经去世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中坚持,可以说是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
在安特生看来,人类文明初期取得的唯一重大成就,就是中国文明——这个几千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文明。
在安特生关于中国的书中,很少有被称为异国情调的猎奇记载,也很少将中国人从人种学的意义上分为几种类型化的模式。 他在中国一直是“外国人”,但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爱。 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男人们瘦而结实,女人们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肥胖,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龙与洋鬼子》 ——左图为1927年德文版,右图为1928年英文版。 图: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最珍贵的是,安特生总是用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表达怜悯之情,所以他的感情特别真诚感人。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时的强盗,他都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来说明。 “中国人天生不喜欢惹事,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农民和商人,当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与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 ”。 将安特生一行人护送到山西省的一名警官解释说:“只有约10%的强盗是因偷窃恶习而成为强盗的,但剩下的90%是不得已而为之作恶的。”
安特生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不被西方理解的陌生之地。
当时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与外界联系较少,许多风俗习惯仍然保留在初期,安特生写道。
直到现在,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某个早期的历史时期(例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 但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相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把中国的民间生活形容为活生生的中世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就像仍然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当时在西方比较流行的3354中国是所有规则的例外,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的3354中国文化神秘而无法理解的说法,安特生并不同意。 他认为中国并不特殊,只是一些不发达地区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 所以,作为欧洲人,他完全能理解中国的一切。 中国工匠的许多方法让熟悉科学和技术的欧洲科学家感到惊讶。 安特生看了中国木匠是如何“解读”巨大的树后,写道。
木匠和棺材匠把树放在锯木框上,把树的一端支撑在地上,另一端以一定角度抬起。 然后,一个人站在树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个人用大锯,准确地把原木切成木板和托梁。 这些匠人的店铺是所有店里最气派的,多亏了坚固的棺材、华丽的华盖,以及大红漆棒等配套用品。
中国人用巧妙的方法,不仅解决了大型道具的短缺问题,而且能使锯头不偏不倚,获得最高的出材率。 因此,德文版有一张照片,在一家叫“义兴木工场”的店里,两个中国木匠锯着比两个人高的木材。
两个中国木匠正在锯比他们俩高的木材。 图: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安特生同情地整理了1840年到1912年的历史。 关于鸦片战争,他写道。
欧洲人对权力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大相径庭,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但在面对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却一败涂地。 欧洲外交官在理论上为所谓的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鸦片贸易、阿洛号事件和欧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蛮行径破坏了他们的“正义”理念。
他试图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理解当时中国四处碰壁的原因,同时从道义上谴责鸦片贸易、“阿洛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的暴行。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这本书中也表达了对欧洲未来的担忧,在该书的第16章《春天的预兆》的结尾写道。
现在我们这些瑞典学生穿着优雅,却很少有机会想起自己国家的风雨,准备考试,享受爵士乐。 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中国学生们身上。 我觉得中国学生精神上更丰富。 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暴风雨和压力的时代,所以当麦秆被风吹倒,根不深的树倒下时,只有强壮的鸟努力振翅高飞。
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来中国几天的旅行者或不懂中文只在欧洲人圈子里生活的记者能得到的。 安特生和其他中国学者一起,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 他不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敬意,也对中国年轻一代充满敬意。 安特生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历经数千年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与古埃及、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被野蛮人破坏的文明不同,中国人从开辟天地之日起,连续四千多年,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繁荣。 他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因此,他说,总有一天,“开启世界新旅程的重任又落在东方人身上”。 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更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院长、环球历史研究院院长、东亚文化谈判学会(大阪,2017—2018年度)会长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2017年起)副会长。 本文获准摘自《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一书导读】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通报/反馈
相关文章

近年美国留学生暴涨,国际学生留学美国、签证、工作申请攻略!
随着疫情的放开,出国留学不再受到限制,国人的留学热情再一次高涨,近日,拥有超过900所成员院校,美国使用最广泛的大学平台——通用申请(Common Appli...
阅读: 2488

金吉列留学与培生PTE达成战略合作!专享优惠来袭!
2022年11月23日,“砥砺前行,共筑未来”——2022 PTE中国峰会在杭州盛大召开,多位驻华使领馆官员,教育类研究机构、企业、学校管理者出席,围绕202...
阅读: 15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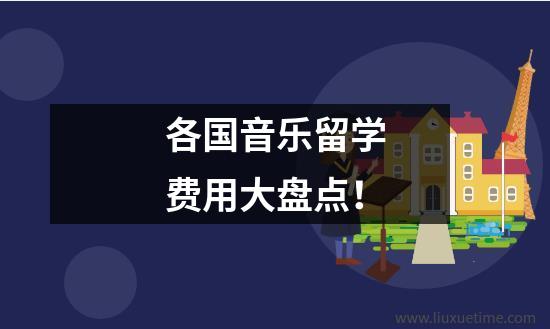
各国音乐留学费用大盘点!
音乐生出国留学到底去哪个国家好呢?正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往往会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各个国家经济、文化和专业学习环境各具特色,所以不少家长和同学在抉择留学国家时...
阅读: 12060

美国博士申请,美国博士学费
花200万读博,和读博期间工资领了200万工资的人都同时存在。同为博士,不同国家和专业的博士待遇可能天差地别。有的国外博士不仅不花钱还能领高薪,有的却要每年给...
阅读: 5673

瑞典留学材料费用大概多少:瑞士留学一年花费多少钱
出国学习的费用,大概就是学费,生活费,还有一些零碎的支出,今天帮大家整理了瑞士留学一年花费多少人民币和在瑞士留学怎么省钱相关问题的解答,供小伙伴参考。一、瑞士留学资金证明金额(1)高中(80-120万...
阅读: 14052

加拿大北部试点移民,加拿大西北地区移民
在12月8日晚上,加拿大驻华使馆举行一个线上活动,推广加拿大的“农村和北部社区方移民试点项目”(有人简称其为“北方移民计划”),这个计划在我们很多留学生和家长...
阅读: 14497

乐山瑞典留学中介地址:瑞典留学学费、申请奖学金、找工作及签证指南
瑞典留学指南指南涵盖了从学费生活费用到奖学金以及签证的过程。我们还介绍了比较有名的大学以及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在瑞典学习意味着您将立足于欧洲北部,并受到一个广受欢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欢迎。瑞典通常...
阅读: 7566

澳洲移民春天到来,新财年澳洲稳拿PR专业大盘点!
上周四的189大放水把在澳洲苦苦等待获邀的小伙伴,和已经放弃拿身PR回国了的小伙伴都打了个措手不及。曾经没有英语八炸连想都不敢想的会计,IT等热门专业的移民分...
阅读: 2061

加拿大留学生移民,加拿大留学移民中介
国内工商管理本科,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场营销硕士,Tina同学于2019 年入读加拿大亚岗昆学院项目管理专业,2020 年继续入读亚岗昆学院商业情报信息系统专业(...
阅读: 8028

鸡娃还是躺平?你想当什么样的父母,经济说的算
“鸡娃”还是“鸡自己”?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引起大讨论。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下——其实你已经下意识地选择了对孩子最好的育儿法,而且这种...
阅读: 5755
更多排行榜
热门文章
1.《骑鹅旅行记》写作背景资料,骑鹅旅行记作者及写作背景
-
1

- 《骑鹅旅行记》写作背景资料,骑鹅旅行记作者及写作背景
- 2024-06-04
-
1
2.瑞典大叔欧尼酱,六个瑞典姑娘在监狱
-
2

- 瑞典大叔欧尼酱,六个瑞典姑娘在监狱
- 2024-01-09
-
2
3.出国留学存款证明什么时候需要,留学开具存款证明
-
3

- 出国留学存款证明什么时候需要,留学开具存款证明
- 2023-12-22
-
3
4.爱尔兰留学签证与移民政策解析
-
4

- 爱尔兰留学签证与移民政策解析
- 2023-12-07
-
4
5.本科护理学专业课程,新加坡本科留学费用
-
5

- 本科护理学专业课程,新加坡本科留学费用
- 2024-01-07
-
5
6.是到德国留学便宜还是去瑞典北欧哪些国家,北欧留学国家推荐
-
6

- 是到德国留学便宜还是去瑞典北欧哪些国家,北欧留学国家推荐
- 2023-11-12
-
6
7.丹麦瑞典,瑞典和丹麦哪个国家好
-
7

- 丹麦瑞典,瑞典和丹麦哪个国家好
- 2024-11-20
-
7
8.学英语好还是小语种好,小语种是天坑专业吗
-
8

- 学英语好还是小语种好,小语种是天坑专业吗
- 2024-03-04
-
8
9.不再阻挡?土耳其:将与瑞典芬兰外长会面,商讨加入北约事宜
-
9

- 不再阻挡?土耳其:将与瑞典芬兰外长会面,商讨加入北约事宜
- 2024-04-14
-
9
10.丹麦瑞典,丹麦vs瑞典
-
10

- 丹麦瑞典,丹麦vs瑞典
- 2024-02-08
-
10
一周热榜

瑞士幸福度,瑞典幸福度
2023-11-03

瑞典留学汽车(「瑞典沃尔沃」2022年第一季度留学生免税车价格公布)
2023-11-04

瑞典留学截止时间(2023北欧留学:盘点北欧各国名校截止时间,提前规划,名校无忧)
2023-11-04

瑞典留学留学体验:北欧留学之在瑞典留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2023-11-04

忍不住竖起大拇指,成都这些瑞典留学机构太赞了
2023-11-04